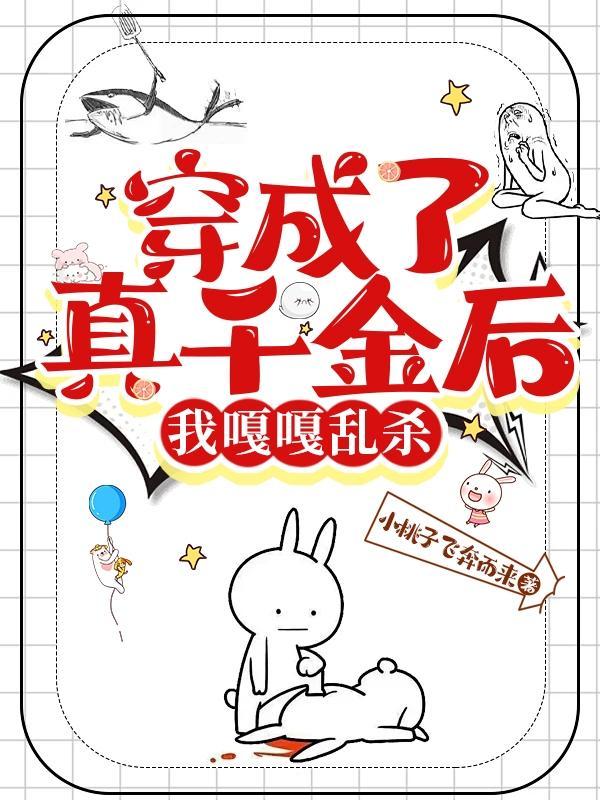帝国小说>病态占有 > 第309章 成千上百根针(第2页)
第309章 成千上百根针(第2页)
顾星渊收回目光,“在我们手里。”
林娴姿拧眉,“什么意思?”
“您想用连盈盈加顾舟山,佐证金通海死因。我们也有我们的目的。暂时连盈盈必须失踪,但我逼顾舟山开口,对您来讲,效果差不多。”
林娴姿眯起眼,幽深难测,像审度的利刃。
割碎剥开顾星渊的面具,“天时地利人和,你们占全了。不像跟我合作,像想法设防帮我。”
连城不由自主握紧手。
她正对顾星渊,背对山下。下午日头偏西,树影在风中招手,一枝枝穿过她,指身后。
她禁不住数树梢,余光往后。
灰碑,绿松,模糊的一片葱郁、死寂,像雾。
雾气里走出一个男人,深沉至极。
黑西装,黑皮鞋,手里同样拿一束白菊花。
花瓣鲜嫩,还裹着露珠,阳光折射的晶莹剔透,衬得来人花白头,斑斑驳驳。
太黯然。
她呆怔,林娴姿清醒,冷了脸,截住男人,“这里不欢迎你来。”
梁朝肃神色淡淡,“我不来,你安心?”
连城如梦初醒,梁朝肃礼数周到,拜祭过莫建鸿,转身注视她。
“连城。”
连城绷紧。
“我认罪,你有一分动摇吗?”
“不,犯罪伏法理所应该。”
“出狱后,穷尽一生,一切,你有可能改变主意,和我在一起吗?”
“我表明过,没有。”
梁朝肃伫立在那儿,镇定自若。
风抚过他修剪利落的短,他眼中以往浓稠狂烈的光与影,褪热褪色,冷冷淡淡,沉淀成波澜不惊的湖泊。
“曾经有人警告我,感情不是谁强,就被谁持有。慕强是人天性,大部分人会被强力统治。但总有小部分压迫不屈,血是热的,脊梁是硬的,你不是世俗懦夫。”
连城一怔。“沈黎川?”
梁朝肃抿唇,良久,“是他。”
连城手脚麻痹,他目光太深入,一瞬过后,又平稳到极致的。
她看不穿,只觉被定格。
梁朝肃面目寡淡,“你的性情,我了解,是我自负有错觉。以为我们感情深厚,与旁人不同,我会成为那个例外。”
连城一动不动,细微的战栗,“你在解释那四年?”
梁朝肃知道她不想听,不理解,无从想象他疯癫的理由。